走进课堂 | 吴晓东:尺八的故事(2)
佚名 网络《尺八》中三种时空的交错使诗的前十句含量异常丰富,短短的十行诗中容纳了繁复的联想,并沟通了现实和历史。诗人的艺术想像具有一种跳跃性,令人想到卞之琳所喜爱的李商隐。废名在《谈新诗》一书中就说卞之琳的诗“观念”跳得厉害,他引用任继愈先生的话,说卞之琳的诗作“像李义山的诗”。《锦瑟》中的“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之所以众说纷纭,从艺术想像上看,正在于联想的跳跃性,造成了观念的起伏跌宕。四句诗每一句自成境界,每一句自成语义和联想空间,而并置在一起则丧失了总体把握的语义线索,表现为从一个典故跳到另一个典故,在时间、空间、事实和情感几方面都呈现出一种无序的状态。又如李商隐的《重过圣女祠》,“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废名称这两句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中国绝无仅有的一个诗品”,妙处在于“稍涉幻想,朦胧生动”。其美感正生成于现实与幻想的交融,很难辨别两者的边际。“常飘瓦”的“雨”到底是梦中的雨还是现实中的雨?“不满旗”的“风”到底是灵异界的风还是自然界的风?都是很难厘清的,诗歌的语义空间由此也就结合了现实与想像两个世界。《尺八》令人回味的地方也在于诗人设计了“海西客”对唐代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想像,这样就并置了两种情境:一是现实中的羁旅三岛的海西客在日本听尺八的吹奏,二是拟想中的唐代的孤馆寄居的日本人在中国聆听尺八,两种相似的情境由此形成了对照,想像中的唐朝的历史情境衬托出了海西客当下的处境,“乡愁”的主题由此在时间与空间的纵深中获得了历史感。诗人的想像和乡愁在遥远的时空得到了异域羁旅者的共鸣和回响。

图为尺八
《尺八》因此是一首融合了叙事因素的抒情诗,在形式上最明显的特征是回避了第一人称“我”作为抒情主人公。一般来说,浪漫主义诗人喜欢以“我”来直抒胸臆,诗中的抒情主人公都可以看成是诗人自己。而卞之琳有相当一部分诗则回避“我”的出现。从诗人的性格来看,卞之琳是内敛型的,不像郭沫若、徐志摩是外向型的。卞之琳自己就说,“我总怕出头露面,安于在人群里默默无闻,更怕公开我的私人感情。这时期我更多借景抒情,借物抒情,借人抒情,借事抒情”。在诗的形式上,则表现为“我”的隐身。而从诗歌技艺上说,卞之琳称他自己的诗“倾向于小说化,典型化,非个人化”,《尺八》就是一首典型的“非个人化”的作品,也是一种小说化的诗。这种“非个人化”和“小说化”除了表现为在诗中引入人物,拟设现实和历史情境之外,还表现为诗人的主体在诗中分化为三重自我。
第一重自我是诗中的叙事者。诗人拟设了一个小说化的讲故事人,从第一句开始,就是叙事者在说话,是一个第三人称叙事者在追溯尺八从中国传到日本的历史,交代和讲述海西客的故事。它造成的效果是使《尺八》有了故事性,读者也觉得自己在听一个讲故事的人讲一个关于尺八的故事以及一个关于海西客的故事。这样就要求读者调整自己的阅读心态,把这首诗首先当成一个故事来读。
第二重自我是诗中的人物海西客。尽管从卞之琳的散文《尺八夜》中可以获知海西客其实就是诗人自己的形象,但从阅读心理上说,读者只能把海西客看成诗中的一个人物。而从诗人的角度说,卞之琳把自己外化成一个他者的形象,诗人自己则得以分身成为一个观察者,可以客观地审视这个自我的另一个形象。这种自我的对象化既与诗人的总怕出头露面,安于默默无闻的性格有关,更与追求诗意呈现的客观化的诗学原则密切相关。
第三重自我则是诗人自己在诗中的显露。我们读下去会看到诗中突兀地插入了“归去也,归去也,归去也——”的呼唤,并重复了两次。我们本来已经习惯了阅读伊始的诗的讲故事般的叙述的调子,所以读到这种饱蘸感情的呼唤会觉得在诗中显得不和谐。但正是这种不和谐却使诗歌有了新的诗学元素的介入,出现了新的张力和诗艺空间。重复的呼唤类似于歌剧中的宣叙调,使诗歌多出了一种带有情感冲击力的声音。这是谁的声音?是叙事者的吗?诗中叙事者的声音是平静和客观的,其作用是叙述故事,营构时空,而“归去也”的喊声紧张、强烈,甚至有些焦灼,是一种充满感情的主观化的呼唤,同时它打破了此前叙事者的连贯的叙述,使故事戛然中止,所以它显然不是叙事者的声音。尽管可能有读者认为这两句“归去也”是人物海西客的呼喊,但是更合理的解释是,这是诗人自己直接介入的声音,带着诗人的强烈感情和意识,尽管它依旧表现为匿名的方式。那么,再看括号中也重复了两次的设问“为什么霓虹灯的万花间/还飘着一缕凄凉的古香?”也可以看作是诗人自己的声音在追问,是诗人自己直接出来说话。也许可以说,尽管诗人一开始想客观地处理《尺八》这首诗,减少自己情感的流露,但是卞之琳写着写着仍然抑制不住自己的冲动,直接喊出了“归去也”的心灵呼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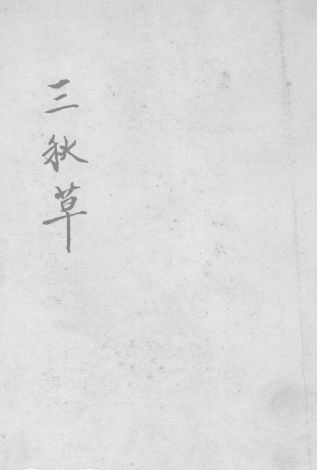
图为卞之琳诗集《三秋草》初版书影
这就是诗中的三重自我。尽管这三个自我在诗中是统一的,是诗人自己的主体形象的分化和外化,但是其各自的调子却不一样。叙事者的功能在于叙述,调子相对冷静和客观。当然这种客观也只能是相对而言,如第十句“独访取一枝凄凉的竹管”,就不单是叙述,还有判断,“凄凉”的字眼就蕴涵有明显的感情色彩。再看人物的调子又如何呢?因为诗中海西客的形象是借想像和心理活动传达的,又是由叙事者间接描述出来的,所以人物的调子基本上受制于叙事者的调子。最后是诗人自己的调子,这是趋向于主观化、情绪化的声音,它流露了诗人的真情实感,又在重复与复沓中给读者一唱三叹的感受,直接冲击着读者的心理深处。
诗中的这三种自我和调子,借用音乐术语,产生的是一种类似于交响乐中的多声部的效果,自然比单声部的诗作要复杂一些。而从总体上看,尽管诗人在诗中外化为三重自我,但无论是从诗的语义表层,还是从诗的结构形式,都看不到诗人自己直接抛头露面,这就是《尺八》的精心之处,它努力达到的,正是卞之琳自己说的“非个人化”的诗艺追求。
肆
卞之琳在日本最初听到尺八的吹奏的时候,油然想起的正是苏曼殊的绝句。那是卞之琳“读过了不知多少遍”的诗作。或许可以说,如果没有苏曼殊这首绝句的存在,如果没有卞之琳对它的“不知多少遍”的阅读,卞之琳可能不会对尺八的乐声如此敏感,也不会从尺八一下子联想到乡愁的主题。换句话说,是苏曼殊的绝句在尺八与乡愁之间建立了最初的关联,这种关联对卞之琳来说就具有了母题(motif)和原型的性质,卞之琳乃至其他任何熟悉苏曼殊的后来者再听到尺八,就会不期然地联想到乡愁。夸张点说,直接触发卞之琳创作《尺八》一诗的动机固然是他在京都也听到了尺八的吹奏,但更内在的原因,则是苏曼殊的诗留给他的深刻的文学记忆。没有苏曼殊的尺八,也就没有卞之琳的《尺八》,苏曼殊的“春雨楼头尺八箫”就构成了卞之琳领受尺八的内涵讲述尺八的故事的至关重要的前理解。
因此,把卞之琳《尺八》与苏曼殊的绝句对照起来看,会是有意思的。当然,这种对比不是从美学意义上比较哪首诗更好。因为就美感而言,也许很多有古典趣味的读者更喜欢苏曼殊的诗。我们是从现代诗和旧体诗两种形式两种载体的意义上来对比这两首诗。
从审美意蕴的传达上,我们可以说,苏曼殊的诗虽短,却更有多义性和不确定性的语义空间。“春雨”到底是下着蒙蒙的细雨,还是像苏曼殊的小注中所说的尺八的乐曲的名字?“芒鞋破钵无人识”描绘的到底是诗人自己的形象,还是专吹尺八行乞的日僧的形象,而诗人只是这个虚无僧的观察者?“踏过樱花第几桥”的是不是诗人本人?这都是非确定的。因此苏曼殊诗也更值得反复吟咏和回味,更荡气回肠。而卞之琳的诗则更为繁复,包容着更复杂的时空框架和主体形态,蕴涵着更繁复的意绪,有着现代诗才能涵容的复杂性。卞之琳的诗更像是智慧的体操,更有一种智性,更引人思索。同时尽管卞之琳的诗包容着更复杂的时空和更繁复的意绪,但是其基本语义还是有确定性的。两首诗的对读,可以让我们进一步思索旧体诗和现代诗各自的比较优势和可能性。
从诗人主体呈现的角度看,苏曼殊在诗中直接展示给我们一个浪游者的形象,但在卞之琳的诗中,我们却捕捉不到诗人的形象,尽管我们能感受到他的声音。我们直接看到的形象是诗中的人物海西客。而从结构上说,卞之琳的《尺八》要复杂得多。前面分析了《尺八》中的三重时空和三个自我,而构成《尺八》结构艺术的核心的,则是一种卞之琳自己所谓的“非个人化”的“戏剧性处境”。
所谓戏剧性处境,指的是诗人在诗中拟设的一种带有戏剧色彩的情境。它不完全是中国古典美学中崇尚的意境,而是有一种情节性,但其情节性又不同于小说戏剧等叙事文学,更指诗人虚拟和假设的境况,情节性只表现为一种诗学因素的存在,而不是小说般的完足的故事情节本身。由此,卞之琳的诗有可能生成一种诗歌的“情境的美学”,而这种情境的美学的出现,堪称是对传统诗学中的意象审美中心主义的拓展。
意象性是诗歌艺术最本质的规定性之一。诗句的构成往往是意象的连缀和并置。这一特征中国古典诗歌最为突出,诗句往往是由名词性的意象构成,甚至省略了动词和连词。如温庭筠的《商山早行》:“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又如马致远的《天净沙》:“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这种纯粹的名词性意象连缀,省略了动词、连词的诗句在西方诗中是很难想像的。不妨对照一下唐诗的汉英对译,比如王维的诗“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的前一句被译成“As the sun sets ,river and lake turn white”。“白”在原诗中可以是一种状态,在汉语中有恒常的意思,“白”不一定与“日落”有因果关系,但是在英语翻译中,必须添加上表示变化、过程和结果的动词turn,句子才能成立,而且这样一来,“白”与“日落”就构成了确定性的因果关系,同时必须引入关联词as。又如杜甫的诗:“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后一句的英译是这样的:“As spring comes to the city,grass and leaves grow thick。”原诗的“春”和“深”都主要表现为形容词的形态,而在英译中,表示时间性的关联词as,表示来临和生长的动词come、grow以及表示确定性的冠词the都得补足。对比中可以看出意象性的确是汉语诗歌艺术尤其是传统诗学所强调的最本质的规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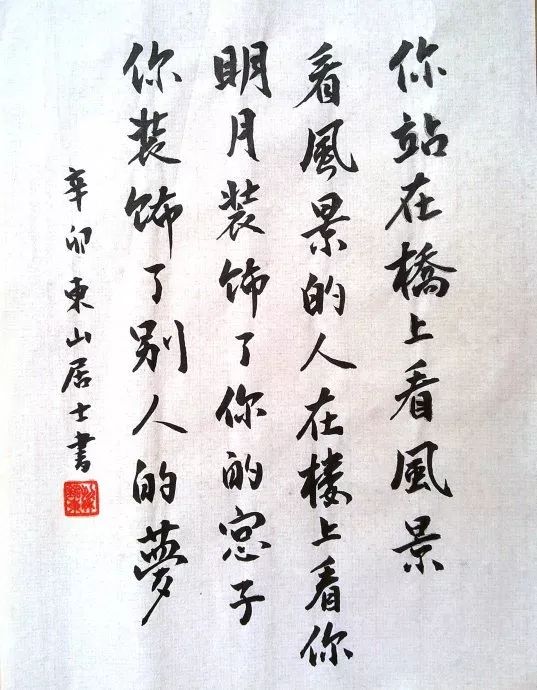
图为卞之琳《断章》书法作品
但是到了以卞之琳为代表的现代诗中,仅有意象性美学,无论对于创作还是对于阐释,都会时时遭遇捉襟见肘的困境,意象性原则因此表现出了局限性。从意象性入手,有时就解释不了更复杂的诗作。譬如卞之琳的《断章》(1935):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这首诗也充满了美好的意象,但是单纯从意象性角度着眼却无法更好地进入这首诗。虽然从桥、风景、楼、窗、明月、梦等意象中也能阐释出古典美的风格与追求,卞之琳的诗也的确像废名所说的那样“格调最新”而“风趣最古”,或者像王佐良所说的那样,是“传统的绝句律诗熏陶的结果”,但诗人把这一系列意象都编织在一个情境中,表达的也是相对主义的观念。“你”在看风景,但“你”本身也在别人的眼里成为风景。如果“你”不满足于被看,“你”也可以回过头去看“看风景人”,使他(她)也变成你眼中的风景。于是,单一的“你”和单一的“看风景人”都不是自足的,两者只有在看与被看的关系和情境中才形成一个网络和结构。这样一来,意象性就被组织进一个更高层次的结构中,意象性层面从而成为一个亚结构,而对总体情境的把握则创造了更高层次的描述,只有在这一层次上才能更好地理解卞之琳的诗歌,这就是情境的美学。《断章》一诗因此就凝聚了卞之琳“相对主义”的人生观和“非个人化”的诗学观念。诗中像《尺八》那样回避了第一人称“我”的运用,也回避了抒情主体的直接出现,而选择了第二人称“你”,使主观抒情转化为“非个人化”的对大千世界的感悟。卞之琳说他的诗作“喜爱提炼,期待结晶,期待升华”,这种追求的结果是他的诗充满了人生哲理。《断章》就是经过诗人精心淘洗,向一种象征性的哲理境界升华的结晶。因此,在卞之琳这里,中国现代诗歌的抒情性开始向哲理性转化。
必须充分估价卞之琳的这种“非个人化”以及这种戏剧性处境的诗艺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中的地位和历史意义。如果说浪漫主义诗人注重情感,那么现代主义诗人更注重智性。卞之琳诗歌创作前期(1930——1937)受到了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以及后期象征主义诗人叶芝、艾略特、里尔克、瓦莱里的影响,在这些诗人的创作中,哲理与智性构成了重要的诗学原则。卞之琳的诗歌艺术也自然偏向智性一极,如果试图最笼统地概括卞之琳的核心诗艺,可以说他倾向于追求在普通的人生世相中升华出带有普遍性的哲理情境,他营造的是一种情境诗。
卞之琳的《尺八》也正是情境诗的佳构。用《尺八夜》中的话,《尺八》这首诗在结构上最明显的特征,是“设想一个中土人在三岛夜听尺八,而想象多少年前一个三岛客在长安市夜闻尺八而动乡思,像自鉴于历史的风尘满面的镜子”。这就是诗人拟想的一种戏剧性处境,一种历史情境。它使诗歌带有一种戏剧性和情节性,表现出卞之琳所说的“小说化,典型化,非个人化”的特征。
伍
卞之琳在诗集《雕虫纪历》的序言中说:“这种抒情诗创作上的小说化,‘非个人化’,有利于我自己在倾向上比较能跳出小我。”这种对“小我”的超越追求与卞之琳的相对主义人生观是互为表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