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出角儿?“不打不成戏”
佚名 网络不管是哪个地域、剧种,艺人们关于学戏的回忆录或传记中,鲜有不提及“打戏”者。各种戏曲文献中,“打戏”一词也随处可见。略举几例:
1
近代昆曲演员韩世昌说: 旧日学戏没有不挨打的,所谓“打戏”。一般教师认为非打不会,不论是谁,即便是亲子侄,因为学戏,打起来也狠着呢。
2
曾在富连成坐科的京剧演员孙盛云说:
俗话说“打戏、打戏”,那年头学戏没有不挨打的。打戏成了施教的唯一或主要的方法。
3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在开封相国寺调查戏剧的张履谦说: 所谓学戏而名曰“打戏”,盖指戏是由打而出来的。
可见,打戏超越了剧种、地域,成为旧时戏曲传承中一种极其普遍的现象。遗憾的是,也许正是由于过于司空见惯,“打戏”这一在戏曲艺人生涯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事件,研究者关注甚少。
打戏,究竟是怎么个“打”法? 给了艺人怎样的体验? 艺人如何看待打戏? 打戏之风为何能够在戏曲界盛行? 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从一个侧面窥见戏曲传承中的某些规律。

一、“学戏没有不挨打的”——打戏与学戏生活
诚如韩世昌所说,学戏没有不挨打的。打戏广泛存在于各剧种、各地域、各种戏曲教学形式之中。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无论科班学戏还是跟私人学戏,想吃这碗张口饭,就少不了挨打。从入科到业满出科,打戏与学戏如影随形,渗入学戏者生活的方方面面,贯穿了整个学戏生涯。
在一些科班里,打戏从入科仪式就 开始了。

如近代河南梆子科班卢殿元科班:
学生入班,教师手持藤条,让学生趴在地上,向学生臀部轻轻敲打三下,名曰: “退退凉壶皮”;接着膜拜“庄王爷”,再拜师,排行,命名,正式收为弟子。(按,“凉壶”为“外行”之意。)有些科班的入科仪式稍有不同,但一样少不了“打”。如1934年成立于河南长葛县的豫剧科班“万乐班” :小孩入科,先给庄王爷磕头,再给白腊杆子(打人用的桑木棍子)跪拜,然后再拜师傅。
入科仪式上的打藤条和跪拜白腊杆子,可理解为一种暗示: 打”是退掉“凉壶皮”、从外行变成内行的途径。它向学戏者宣告了教戏打人的合法性与学戏挨打的必然性。在程序上,将打藤条和跪拜白腊杆子置于拜师傅之前,意味着在是否能够进入梨园行这一点上,打戏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打”是学戏的法宝,打人的藤条和白腊杆子比教戏的师傅更重要。
打戏及其工具被纳入入科仪式中,同行业神一起进入学徒的精神信仰层面,成为戏曲艺人职业认知的一部分。这种人为的神化,使“藤条”、“白腊杆子”在警戒、威吓学戏者的同时,也起到了从信仰上约束人心、防止反抗的作用。
入了科,打戏就伴随着学戏生活正式开始了。打戏的名目众多,练功时出错了要打,学戏慢了要打,舞台上没要下“好儿”(指观众的喝彩)要打,演错了、演砸了更要打。一人犯错,全体挨打,这是“打通堂”,或叫“满堂红”。有的先生知道学生挨打后心里不服,特意找碴儿再打,这叫“揭嘎渣儿”。更有甚者,演好了也得挨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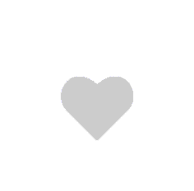
例如某某的戏唱好了,先生也很满意,他等你洗完脸后,便把你叫到跟前,说: “XX,今天的戏演得不错! 去,把那个刀劈子拿过来。”学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心中提心吊胆,不知什么地方唱错了,板子又挨上了。这个刀劈子虽说不愿拿,然而,也得硬着头皮去拿。拿过去还得双手捧着,恭恭敬敬地递给先生。先生接到后: “伸出手来! ”乒乓打两下 。“伸出那只手来!” 又是两下。“今天的戏唱得很好,今后还要照这样唱,记住! ”当学生的这时才算一块石头落地了,向先生鞠个躬才能走开。(田敬涛整理《新乐县杜固科班情况》,《河北戏曲资料汇编》第14辑,第119页)
犯错误时,“打”是为了惩罚;演好了,“打”又取代了应有的奖赏,而成了警戒、鼓励的手段;“揭嘎渣儿”就纯粹是对学生的暴力压制了。打戏,成为师傅施教的主要甚至唯一的手段。
除了练功、演戏之外,打戏也被应用于学徒的日常生活管理当中。每个科班都有成文的或不成文的班规。违反了这些规矩,当然也是要挨打的。比如吃饭时说话要打,私自出门要打,等等。
甚至没有错误,也要挨一些莫名其妙的打。
比如河北新乐县杜固科班(1909年成立)在每晚睡觉之前每个学生要打四棍,以让学生安安生生睡觉;前面提到的卢殿元科班规定三天一个小“满堂红”,五天一个“大满堂红”。这种打戏,目的是以靠频繁的打戏来震慑学生,迫使学生老老实实地遵守科班的生活纪律,没有胆量也没有体力去调皮滋事。
以上所述,只是一般科班里打戏的情形。但打戏绝不仅仅存在于科班之中,那些写给私人学戏的手把徒弟也一样免不了挨打的命运。不仅学戏要打,伺候师傅师娘、给师傅家干活稍有差错也要打。打戏的工具、花样较之科班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打戏如此盛行,以至于在很多人、包括梨园行以外的人心中,它成为学戏生活最重要的特征。
对艺人来说,打戏则是刻骨铭心的痛苦记忆:
打
打戏的痛苦记忆
京剧演员李洪春一天曾挨过十六次“打通堂”;
韩世昌幼年学习昆剧时,曾两次被打“死过去”(指昏迷);
据幼习河北梆子的演员李桂春(艺名小达子)回忆,与他同科学艺的小顺子,八岁时因下腰下不好,被教员生生踢死;
……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几乎每一个艺人,都有一部血泪斑斑的“打戏史”。频繁、残 酷的打戏,给艺人带来的首先是肉体上的折磨:
挨打以后,轻的,两股青紫,行动不便;那被打得重的,两腿就皮开肉绽,鲜血迸流。还得自己买鸡蛋,调鸡蛋清敷上,这样可以好得快一点。但是想因致伤而中断学戏、练功和演出,那是一点门儿也没有。在这当口,棒伤要崩裂,疼痛难耐。愈合、崩裂,再愈合、再崩裂……这样反复多次才能痊愈。(孙盛云: 《学艺演戏忆当年》,见《京剧谈往录》四编,北京: 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68页。)
打戏也给年纪尚幼的学徒们带来了巨大的精神痛苦。孙盛云如此描述自己坐科时的感受:
我在富连成科班坐了七年“大狱”,每天提心吊胆,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挨一顿没头没脑的暴打。那蘸水的刀坯子和藤子棍打在身上火烧火燎,登时鼓起一道肉棱子。每回挨打我都从心里往外哆嗦。
因为学戏时挨的打太多了,且挨打时多是趴在板凳上打屁股的,“啃板凳头出身”就成了许多艺人的自称。打戏,已经成为标志艺人特殊身份的烙印。
打戏与学戏似乎是一对孪生兄弟。名目众多、花样百出的打戏,涵盖了艺徒们学戏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练功学戏到日常生活,从惩罚到鼓励,可谓无孔不入、无所不能。打戏,就这样与戏曲传承、与艺人的学戏生活纠结在一起,并成为艺人不堪回首的惨痛记忆。

二 、“不打不成戏”——打戏与口传心授
耐人寻味的是,那些饱受打戏之苦的艺人,对于打戏,深恶痛绝的少,持某种程度上的认可态度的多。评剧演员新凤霞的话颇有代表性: “练功学戏挨打我是心甘情愿的。”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许多梨园行的人,虽然有条件让后代在自己家里接受戏曲教育,但依然要将其进科班去“坐大狱”。原因之一便是怕管教不严,难以成器。富连成科班本不收名家子弟,谭鑫培亲自说情,将孙子谭富英送去学戏,并与科班约法三章,其中之一便是“与所有学生同样待遇,决不特殊照顾” 。所谓“同等待遇”,当然免不了挨打。谭鑫培与谭小培父子自然是明白这一点的,甚至可以说正是冲着这一点才将谭富英送进科班的。谭富英的儿子谭元寿,也是富连成科班出身。像谭家父子这样的戏曲艺人很多。在富连成三科之后,班中的内行子弟越来越多。这固然是对富连成办班规模、教学质量的肯定,却也包含着对科班教学方法(包括打戏)的认同。
除了科班,戏曲艺人让子女拜他人学戏、甚至“易子而教”的,也不少见。而那些自己教子女学戏的艺人,也少不了对子女拳脚相加。常香玉的父亲曾因教戏时打女儿太狠而被误以为是人贩子。
在早期的新式戏曲学校里,打戏也被继承下来。由焦菊隐担任首任校长的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吸收了西式学校的办学优点,不拜祖师爷,开设文化课,在生活管理上也很进步,却没有完全废除旧科班打戏的做法。即使在新式戏校纷纷成立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仍然有很多戏曲教师坚持认为“戏是苦虫,不打不成”,“如果不打,一辈子也学不出来”。尤其是学技术,必须用打来辅助。(史若虚:《戏曲教育工作十年散忆》,《戏剧报》1960年第2期。)
不难看出,艺人对于打戏的认可程度相当高。用一句戏曲谚语来说,这叫“ 不打不成戏”。

为什么“不打不成戏”?
“打戏”与“成戏”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 如果仔细追究,“打戏”之所以能够“成戏”,“成戏”之所以需要“打戏”,二者之间的联系,就存在于戏曲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之中。
首先,在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下,打戏是督促学戏的一种便捷方法。
戏曲是一种活态的艺术。它以人的身体为载体,戏曲艺术的习得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按照一定规律塑造人的身体的过程。身体既是传承的工具,也是传承结果的最终体现。戏曲传承活动与身体的天然联系,为打戏提供了便利。尤其是练功时,当学戏者某个部位的动作出现错误时,很容易引发伴随着纠正错误的针对该部位的殴打行为。比如,下腰时下不好,很可能就要被踢腿或者腰。对那些打“飞脚”太慢的学生,教师就用藤杆子快速地抽打,以迫使其加快速度。
戏曲长期以来依靠口传心授进行传承,这种传承方式缺乏文字依凭,以教戏人的口头传授、身体示范和学生的模仿、体悟来实现传承目的。这对教戏人的认识、表达能力和学戏人的记忆、理解能力都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一旦其中一方不能达到这个要求,比如教戏者自身艺术水平有限,无法提供良好的示范,或者艺术水平足够但语言表达能力不足,难以清晰、准确地传达表演的要义(何况戏曲表演自身也有其“不可言说”的一面);或者教戏者水平足够而学戏者天资太差,窗户纸屡捅不透,都会造成传承活动无法顺利进行。在口传心授中,除了教戏人无形的、转瞬即逝的声音和形体动作之外,找不到固化的、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物质”来辅助理解和记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达成教学目标,无计可施的教戏人会很自然地使用打戏这种简单粗暴却便利的方法来督责学戏者。
戏曲传承活动的主体——艺人对此也是深有体会的。如河北梆子老艺人贾玉林所说:想起那时候挨打真可怜,可仔细想想,不打还真不行。如果那时管得不严,决学不会那么多戏。不象现在有剧本,忘了可以看看,我们那个时候完全靠死记硬背。
可以说,口传心授的传承方法本身就蕴含着一些诱发打戏的因素。在这种传承活动中,打戏虽然不是艺人教戏的必然选择,却是一种督促学戏、达到教学目的的无奈而又便利的选择。这是形成“不打不成戏”观念的原因之一。
其次,戏曲口传心授重模仿练习轻启发诱导、重经验轻理论的特点使打戏在某些场合显示出了一定的效果。
一位京剧老艺人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回忆起挨打的经历时泪流满面,却仍然说: “不打学不磁实”。李桂春曾经怒打过自己的儿子李少春,原因是: “这样他只能痛一次,也比他由于练功开玩笑摔死强! ”可见,无论是挨打的学戏者,还是打戏的教戏人,都认为打戏是有用的。
那么,打戏的作用究竟何在?
最显而易见的是,它以殴打来惩罚学戏中的错误行为,迫使受教者形成正确的、规范的行为方式。这种作用在练习基本功阶段尤为明显。这与口传心授注重模仿习练,而不重启发感悟的特点有很大关系。唱、念、做、打各项功夫,无不需要大量“刻模子”式的反复习练,以达到一字一腔严谨、一招一式准确的规范化教学效果。打戏的纠错功能在这种练习中能够最充分地显现出来。比如,艺徒练功时,如果动作不快,不帅,就要挨打;在藤条和刀坯子的挥舞下,为了避免挨打,身上的动作就必须帅、快、美。学习唱、念,精神不集中,多次记不住,也要挨打。这种教育方法虽然难免消极,却能迫使学戏者将肉体的痛苦转化为精神上的自警自励,从而改正错误,养成正确的行为习惯。艺人们“不打不磁实”、“不打不成戏”的经验,多是从这种练习中得出的。
也有的时候,打戏本身并未真正发挥作用,一些偶然因素使其目的得以实现。但因为这些偶然因素未被充分认识到,打戏的效果便被夸大,“不打不成戏”的观念借此得以强化。韩世昌曾有这样的经历: 夜里散戏后学唱,困倦不堪,没有唱会,被打“死过去”。回过气来以后,哭哭啼啼了一会儿,居然会唱了。先生说: “是不是? 不打不会、非打不可。”对于这件事,韩世昌分析道:
是不是非打不会呢? 是不是打一顿以后居然就会了呢? 这里面有道理。原因就是先生教戏是注入和死灌,不容你消化,不容这些新东西在脑海中酝酿,所以死教死不会。往往我们学一段唱,头天死唱死不会,待睡了一宵以后,第二天起来无意中一唱,唱对了、唱会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经过一宵脑海中的酝酿消化以后掌握了,所以大脑疲劳发滞的时候就不应该强迫他记忆了。老一辈的人不懂得教育心理学,非让当时会不可,不会就死打一顿。孩子哭泣,头脑经过一次剧烈的刺激以后,脑海一活动,说不定就真剋化开了,也就唱出来了。所以使得老一辈认为一打就会,非打不可。
这种情况,可谓“歪打正着”。从这种事例中得出的“不打不成戏”的经验,当然是很片面的。正如韩世昌所说的那样,其原因是老一辈的人不懂教育心理学。但是,中国本来就有重经验、轻理论的传统,戏曲的口传心授更是这样。戏曲通过艺人一代代传承下来,关于戏曲传承的理论,却长期处于无人总结的状态。前辈艺人留下的,不过是一些散漫的、枝节的经验介绍。艺人们既无理论可学,也因文化水平太低而不具备归纳总结的能力,只能凭借前人和自身的经验来传授戏曲。因此,从亲身实践中得出的经验,尽管片面,也就难免被奉为真理了。

再次,口传心授的“人治”特点赋于了打戏情感上的积极意义。
戏曲教育家、理论家朱文相认为,戏曲的口传心授是一种“人治” ,教戏者个人思想修养、艺术造诣、才能见识对教学质量的优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戏曲传承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此言不虚。虽然师傅在名义上负有传授技艺、培养徒弟的责任,但在实际中,师傅传授什么、如何传授,完全由师傅说了算。而且,旧时艺人又多有保守思想,不肯轻易授艺于人。对徒弟“留一手”、不肯尽全力教戏的师傅不在少数。因此,那些尽心教戏的师傅就显得格外难得。
在这样的背景下,打戏就不是“虐待”,而是师傅尽职尽责、要求严格的表现了。严格要求当然是好事。打戏得到认可,打戏人的良苦用心也得到了充分的理解。饱受打戏之苦的侯宝林说:
打人这种“教学方法”当然不好,但老师这种严格要求的精神还是值得发扬的。这对我后来学东西快,很有好处。
老艺人刘元芳也很能理解师傅的苦“手”婆心:
他们打学生并不出于本心,谁也不愿打。他们打学生都是含着眼泪打,因为他们入科班时都尝到这个滋味。古人说: “人不打不成才,玉不琢不成器。”打,是为了出息学生,让学生多学些东西,学快点,否则,感到学生科满学不到东西,对不起学生。另一方面,说起来是谁谁教的,脸面值千金。所以必须要打,只有打,才能出息人才。
打戏不仅未使学生与师傅疏远,反而增进了师生感情。闽剧演员郑奕奏学戏的时候也挨过不少打,他说自己“在艺术上求进步的心迫切以后,对于师父的严格,丝毫不埋怨,反而与师父更亲近。
打戏是严格要求,也是关心爱护。看似不人道、不合理的打戏,艺人们却从中提炼出积极的、合理的因素。他们从这种严格要求中受益,不仅完成了在科的艺术学习,而且将之带到以后的艺术活动中,成为伴随他们一生的财富。打戏所体现的“关心爱护”,压倒了它所带来的肉体与精神之痛,使艺人甘心忍受藤条与刀坯子的惩罚,甚至不乏感恩之情。
在艺人看来,打戏所体现的严格要求与关心爱护,源于师傅把徒弟培养成才的期待,虽然这种期待是以“恨铁不成钢”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打你,是因为师傅觉得你是块料子,能成才。正像新凤霞所说: “师傅只有心爱的徒弟才打你,否则师傅乐得闭目养神,抽烟袋,挣钱省心。”
这正暗合了心理学中的“皮格马利翁效应”: 赞美、信任和期待能使人增强自信,获得一种积极向上的动力,使才能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以尽力达到对方的期待,避免对方失望。当打戏中所蕴含的信任与期待被学戏者感受到,打戏就从一种负面的惩罚措施转化成了正面的精神鼓励,并对他们学戏的行为与结果产生积极的影响,使之努力学戏、出人头地以不负师傅的期望。当他们在艺术上有所成就时,回顾打戏的经历,在感激师傅的同时,也更加认可了打戏的做法。
但事情的另一面是,对打戏的正面理解和认可,也使这些“打”出来的艺人在教戏时更容易扮演自己师傅当年的角色。在没有严格的制度明确制止打戏的社会条件下,从学徒到师傅,打戏就这样伴随着艺人的养成过程和戏曲的传承过程被继承下来,“不打不成戏”的观念也随之代代相传。
综上所述,“不打不成戏”是戏曲艺人教戏学戏的一种经验。“打戏”与“成戏”之间本质上并无必然联系,因而这种经验具有片面性和局限性。但是,在传统的口传心授活动中,打戏是督促学戏的便利选择,并在某些场合显示出了一定的作用,打戏行为中所蕴含的情感因素也促使艺人认可了打戏的做法。“不打不成戏”的观念就产生于这样的基础之上。
必须强调的是,说“不打不成戏”的观念与戏曲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有关,不是说口传心授必然导致打戏,而只是说口传心授中蕴含着一些诱发打戏的因素。这些因素要真正转化成现实中的打戏行为,还需要合适的外部条件。
怎样才能出角儿?“不打不成戏” 高清电子版乐谱歌词图片是器乐学习网于2022年03月08日 16:01:42更新分享的戏曲知识;资源收录于戏曲知识栏目中;器乐学习网免费分享怎样才能出角儿?“不打不成戏” 简谱与五线谱歌谱图片,欢迎在线免费下载;器乐学习网无需注册会员,直接免费下载各类乐器学习资源及乐谱。
![评剧简谱[尊厅长]杨三姐告状选段](http://m.qiyuexuexi.com/templets/default/img_2022/img_loading.gif)